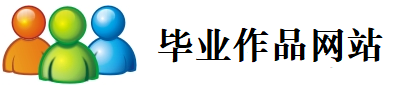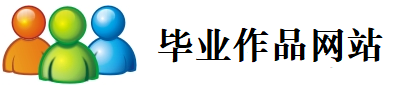为真实的世界设计
作为一个设计师,在我们为现代物质丰富的生活而设计的时候,如各种高档的汽车、计算机互联网产品和数码产品等,不幸的是,还有很多领域被设计忽略了,如偏远地区的学校教具设计,留守儿童的生活物品,农村生产农具,干旱地区的饮水系统设计,贫困地区的医疗器械,盲人的生活用品等,所以,一个设计师如何让自己的设计服务于弱势群体更能体现出设计的伦理观,设计的伦理观主张设计师应该承担社会的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设计不应该只是为了获得特定的商业利益,设计更应该关注被忽视的少数人。
每次看到设计杂志上报道某些设计师所倡导的“设计就是好生意”等类似的宣言时,心里有说不出的不爽,但是自己也跳不出圈子,生活和工作在这种体制下,只能把有些东西放在心里,有时候人还是需要理想一点,理想主义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最简单的快乐。
最近在写论文,收集到了这份资料,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期待着最真实的设计为最真实的世界。
真实的情况是,人们并不要求工程师为安全而设计。要是仍然不行动就是犯罪了——因为有足够的事实说明,我们的行动将能够引起改变,车祸会减少,高速路上将不会再有屠杀……到了行动起来的时候了。——罗伯特•F.肯尼迪
离开学校以后,我最早做的一项工作是设计一种台式的收音机。这是个裹尸布一般的设计:设计电子机械装置的外壳。这是我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接触这种外表设计、样式设计或者说是设计整形。那种收音机是战后市场上最早兴起的轻便型台式收音机之一。尽管我部分时间还在学校做事,我还是觉得毫无把握,被这一套庞大的工作弄得诚惶诚恐,尤其当我想到我设计的收音机是一家新公司的唯一的产品时。一天晚上,我的雇主,G先生带我来到他公寓的阳台眺望中央公园。他问我是否已经意识到了为他设计收音机的责任。
由于我觉得这种问法并不可靠,所以便开始大谈起市场标准的“美”和“顾客满意”的话题来。他打断了我。“是的,当然,你说的都对,”他继续道,“但是你的责任远比那些都大。”接着,他又发表了一通他自己(往大里说,包括设计师)要对他的股东,特别是对他的工人负责的陈词滥调:“你就站在我们工人的角度上想想你的收音机承担的责任吧。为了生产,我们在长岛建了工厂。雇了大约600个新工人。工人们来自于许多州,佐治亚州、肯塔基州、阿拉巴马州、印第安纳州,他们几乎就是连根都挪到了这里。他们会卖掉自己原先的住所,然后又来这里买新的。他们会在这里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社区。他们的孩子也被从原来的学校拽了出来,塞到了另外一个学校。在他们那块新的土地上,为了他们新的需要,各种各样新的超市、药店和维修站都会开张。现在,设想一下收音机卖不出去。一年之内,我们都得把他们辞掉。他们将没法付房租,没法买车。前滚动不起来,商店和银行都得关门;房子又得拿出去卖掉。他们的孩子也必须地换学校,除非他们的老爹找到了新工作。头疼的事儿太多了,这还没说到我的那些股东呢。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犯了一个设计的错误。那就是你的责任所在,我敢保证学校里从来没有教过你这些!”
由于年轻,坦白地说,我当时被震住了。在G先生那一封闭、狭隘的市场辩证法体系里,所有的说法都是有道理的。这么多年之后,从一个高些的位置往回看,我必须承认设计所要对他投放市场的产品的设计方式负责。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太狭隘。设计师的责任必须远远超越这些想法。在他开始设计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他的社会和道德判断就必须起作用,因为他必须做一个判断,一个先验的判断,即人们让他设计或再设计的产品是不是完全值得他去做。换句话说,他的设计是不是站在社会利益这一边。
食物、居所和衣服: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人类生活必需品。随着社会日趋精致复杂,我们又在这个单子上加上了工具和机器,因为它们能够使我们生产其他的三项。但是,人类有比食物、居所和衣服更多的基本的需求。千百年来,我们理所当然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喝着纯净的水,但如今这幅图景却遭到了急剧的改变。尽管空气、河流和湖泊污染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是,普遍的,工业设计和工业本身显然对现状负有一定的责任。
外国人眼中的美国形象常常是电影创造的。那是个让人宁可信其有的童话世界,到处都是灰姑娘喜欢的“安迪•哈迪上大学了”和“雨中曲”之类的事情,它比情节和明星更直接而且下意识地感动了我们的外国朋友。它传达的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环境,一个被各种触手可得的新式小玩意装点的环境。
在80年代,我们出口各种产品和新鲜玩意。随着我们对我们乐意认为是自由的世界的另外一部分地区进行愈演愈烈的文化和技术的殖民,我们也忙着出口环境和“生活方式”,1982年再尼日利亚看“我爱露西”的重播或者在印度尼西亚看“鬼门关2”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已经不稀罕了。
设计者—策划者对几乎所有的产品和工具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因而也就应该对我们在环境上犯的错误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不仅要对差的设计负责,还要对没有履行责任负责:由于抛弃了责任,没有发挥他的创造性才能而负责:“没参与”或者“敷衍了事”也要负责。
如果我们把一个三角形看做是设计的问题,我们会很容易看出工业及其设计师关注的只是三角形顶端的那一小部分,却忽略了真正的需要。
让我们以微机为例。无论是在工作与在家工作之间的关系上、与商业相关的和与个人相关的问题上,还是在数字的处理程序、信息储存和恢复等方面,微机被引入办公室和家庭都给交流机制带来了许多重要的改变: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它改变了人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无论在家还是在办公室里,设计师们用计算机处理他们的工作成了很平常的事。许多电脑是家用的,还有一部分小型的电脑是给办公室准备的,他们都有玩游戏和其它电子娱乐项目的功能。剩下的,无论他们是否装有磁盘驱动器、磁盘或者磁盒存储,看起来样子都差不多。制造商和设计师已经开始试着改进键盘和显示器终端,但是,这些企图顶多不过是在表面问题上下功夫。他们所处理的是外壳,又是也改一改键盘按钮的样子。但是,要想真正弄明白微机和文字处理软件的问题,无论是制造商还是设计师都必须检验跟这一工具的应用相关的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
1. 对于键盘上各种字母、数字、符号和命令的安排是不是根据日常应用和手的舒服来的?(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打字机的键盘的设计从人机工学的角度看是很失败的)
2. 黑屏上的绿色字母是不是很舒服,它是否造成了眼睛疲劳,而且还不容易辨识?Commodore 和Osborne 电话还通过他们的视觉终端在黑屏上提供琥珀色。对于一台3000美元的电脑来说,应该再顶多花30、50美元就能“任意”挑选背景和数字以及字母的颜色。
3. 对于大多数使用微机的人来说,荧屏上字符的大小是否合适?显然,字体的多样应该是很容易能够做到而且是应该加上的内容。
4. 电脑的记忆是否应该想办法保护,以避免因停电、电磁爆等带来的损失?许多用文字处理软件的人在他们所在的城市的电路出问题的时候曾经丢过整整一篇博士论文、参考书目或者一本书的一部分。多加一个设备多花不了40美元,但是仍没有常规的设置。
5. 显示器的角度看起来是不是正好?它是否能被调控(手控)以适合带着双焦或者三焦眼镜的人呢?
6. 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的各种指令功能会不会被两个直接使用的群体不小心漏掉了呢:那些处理数字,以及那些使用文字处理的人?
7. 键盘——或者放置键盘的平面——是否能因人的不同身材而降低或升高,甚或还有些躺在轮椅上的人呢?这样的一些调整是机械性的,而不是点字的或水压的;它们施行起来花钱不多,而且几乎不会出什么错。
8. 使用者的椅子是否能够很容易上下调节?
9. 与电脑一块的操控指南以及结构磁盘、碟片和录音设备是否简明易懂?
10. 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者被迫使他(她)自己适应的机器,而不是所谓“与用户友好相处”,或者,鉴于它有着光滑的平面、运算速度快而“宽大为怀”呢?
上面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闲言碎语,而且我们还可以继续加上其它内容。罗伯特•弗兰克博士对纽约的芒特西奈医院做了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他发现许多患有视觉疲劳、视网膜脱落、视幻症、头痛、背痛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在工作中都经常使用视频展示终端和家用电脑(《万象》,1983年10月18日)。这些让人不能饶恕的、缺乏革新的设计的存在,其原因在于微机市场上存在的激烈竞争。尽管改进上面提出的10个问题在零售市场上意味着要提高400美元(粗略地说来也就是一个个人文字软件零售价格的一半到八成左右),而实际上大规模生产多花不了200美元,但是,粗野而又原始的市场战略,尤其是美国人所谓的自由企业制度,要求企业交到股东们手里的财务报表必须在每一个90天理都能体现出利润的增长,因而,市场竞争的喧嚣阻碍了设计的改进和提升。
作为一个设计师,我的观点是必须根据办公室和家庭的实际情况、人的特点和使用的方便去做。工业企业及其所掌握的设计师还没有让他们自己把我们画的那个三角形巨大的底座作为考虑的对象。
只是标签换了一下。我们把“设计的问题”换成了“国家”。从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在谈论偏远地区时,这样看就一目了然了。如果我们让整个三角形代表包括南美和美洲中心国家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地区,我们就会看到其目的性的倾向。几乎所有这些地区的财富都集中在一小部分“缺席的地主”手中。其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去过南美国家,但是他们却对之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开发。设计成了一个小圈子的奢侈品,这个小圈子包括了所有国家的技术、金融和文化“精英”。而“内地”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著印第安人既没有生产工具也没有睡觉的床,他们没有学校也没有医院,他们甚至从来就没有闻见过从设计师的作坊飘出来的气息。正是这一大群贫困而又被剥夺的人代表了我们这个三角形的底座。如果我说这同样说明了非洲、南亚和中东地区的真是情况,估计没几个人会有异议。
不幸的是,这个图表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内部的城市和乡村,学校系统中我们所使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具,我们的医院,医生的办公室,诊断设施,农具等等,都被设计忽略了。尽管在这些领域中,新的设计会零星地出现,但这往往是一种研究突破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对于真正需要的真实反应。这里,我们必须把设计师服务的这些工作指派给三角形顶端的那些人。
但是我们又一次更换了标签。现在我们把它叫做“世界”。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并没有受惠于设计师,对这个问题的真实性还能有怀疑吗?
我们的创新精神都跑到哪里去了呢?这并不是一种要把我们的生命中的乐趣都抽走的企图。毕竟,想花钱买“成人玩具”的人就应该得到,这在一个丰裕社会中只是一种正当的权利。在1983年的美国,事实上几乎没有专门为家庭生产的收音机。有些是在美国组装起来的,但是部件却是来自台湾、韩国和香港。最多3、5年之内,它们将来自中国大陆、印尼或那些我们还没有染指过的中美洲国家。索尼、日立、松下、爱华的更新换代都很快。他们生产120多种型号的台式收音机,其区别来自于它们的用途、外观和特殊用处的差异。这种情况很快也会在录音机、电视机和照相机身上出现。这并不是说公司里卖出去的每一种产品都必须品质优良。毕竟,正如许多书商那样,尽管他们往最好的销售担子里掺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垃圾,但他们每年也设法出版一些有价值的著作。
那些想在整个三角形中做出点成绩来的设计师(问题、国家或世界)常常发现他们自己被说成是为少数人设计。这种指控是完全错误的。这反映了在职业操作上的误会和错误认识,对于这些错误认识的本质必须加以检验。
让我们假定一个工业设计师或一个完整的设计机构其工作的范围完全处于这一章和其它章节所勾画的人类需要的框架中。那么,工作的任务又由什么组成呢?它包括各种用于学龄前、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和博士后以及各种研究项目的设计。也会有一些为特别领域设计的教育设施,这些领域包括成人教育、为智障、社会底层和残疾人提供的知识和技能培训,还有特殊语言教育、职业再教育、凡人的改过自新,以及精神病等。除此之外,围绕着人展开的新技能教育应该给他们的生存环境带来彻底的变革:从贫民窟、少数民族聚集区、农村贫困地区到城市;从澳洲土著到技术社会中的人;从地球到太空;从英国宁静的乡村到北极严寒中的生命。
我们假定的机构所从事的设计工作应该包括医疗诊断仪器,医院设备,牙科器械,外科工具的设计、发明和改进,包括为精神病医院设计仪器、器械和设备,包括妇产科设备以及为眼科医生准备的诊断和训练仪器等等。其工作范围从能够更好的读解的家用体温计到一些特殊的器械,如心脏起搏器、心脏读解器、人工器官、移植器官,而且他还要为盲人设计简易的解读器,改善的听诊器、分析仪和助听器。以及更新性的按日分配药丸的器械。
设计的机构还应该使自己关注为家庭、工业和交通运输及其他领域涉及安全的设备,而且这些设备不应该给河流、湖泊、海洋、大气造成化学和热污染。世界上75%的人生活在贫困、饥饿中,这些人显然需要我们的设计机构在其时间表上挪出更多的时间来给予这些人以关注。但是,不仅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需要特殊的帮助,这种特殊的需要在我们的住所周围到处都有。肯塔基和弗吉尼亚西部黑人矿工的肺病只是各种职业病中最寻常不过的一种,它们中的许多都可以通过对设备的再设计加以避免。
研究设备一般是些从事相互关联、临时配备起来而又精巧的装置,但是从事高级研究项目的人却常常苦于没有被理性设计的设备。从雷达、望远镜到简单的化学实验用的烧杯,设计都远远地落在后面。老迈之人需要什么样的设计?孕妇和胖人需要怎样的设计?全世界那些觉得被社会疏远而倍感孤独的年轻人需要什么?公路运输又需要什么样的设计呢?(美国车的确是最有效的杀人机器,有了它,机关枪就算不了什么了)
这是不是在为少数人设计?问题是我们所有的人在生命的某一个点上都是孩子,我们整个一生都需要教育,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经历着青年、中年和老年。我们需要老师、医生、牙医和医院的帮助和建议。我们所有的人都属于有特殊需要的群体。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迁移、交流、产品、工具、住房和衣服。我们必须有干净的水和空气。作为一种物种,我们需要探索的挑战,空间的许诺和知识的丰富。